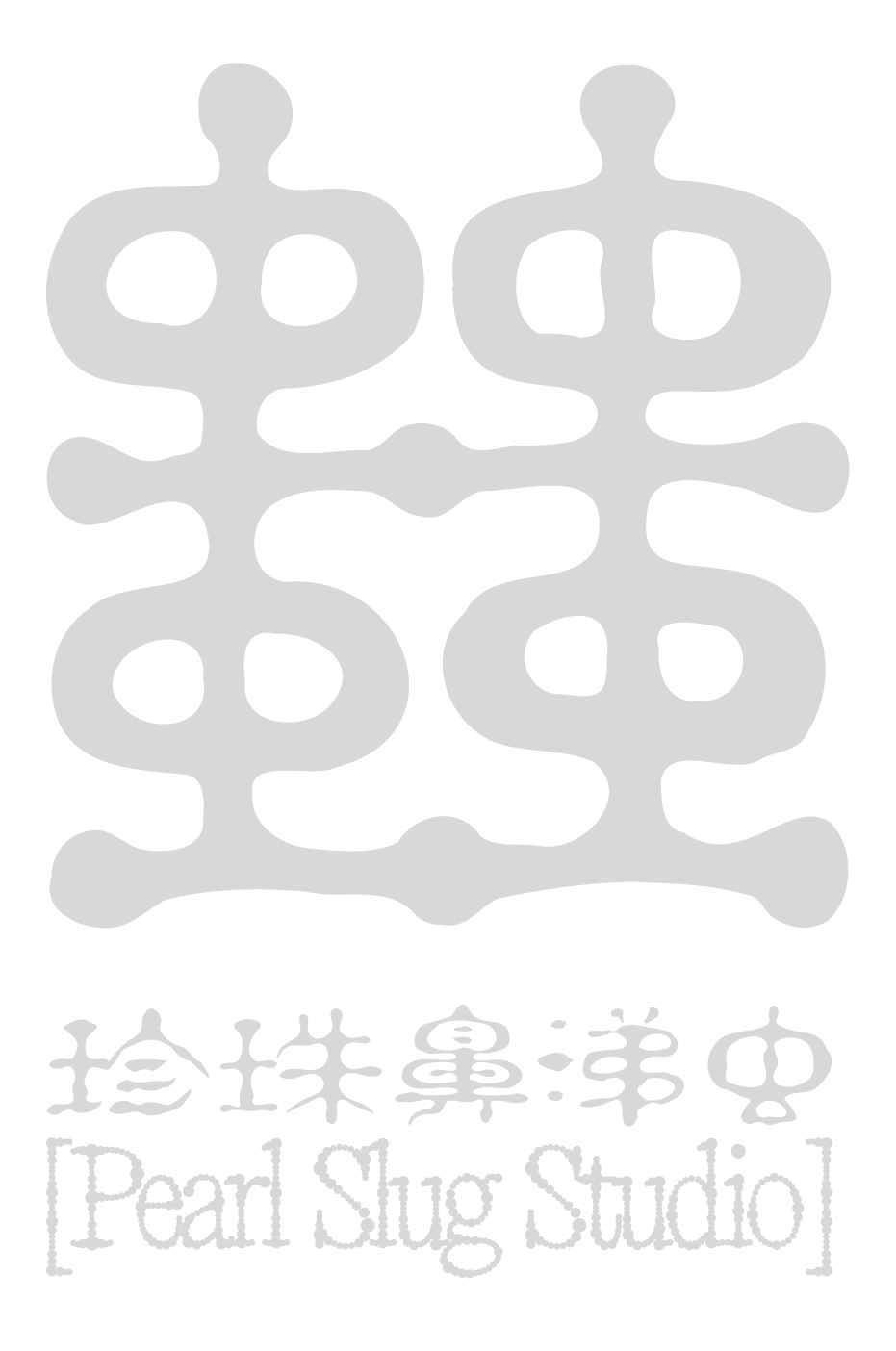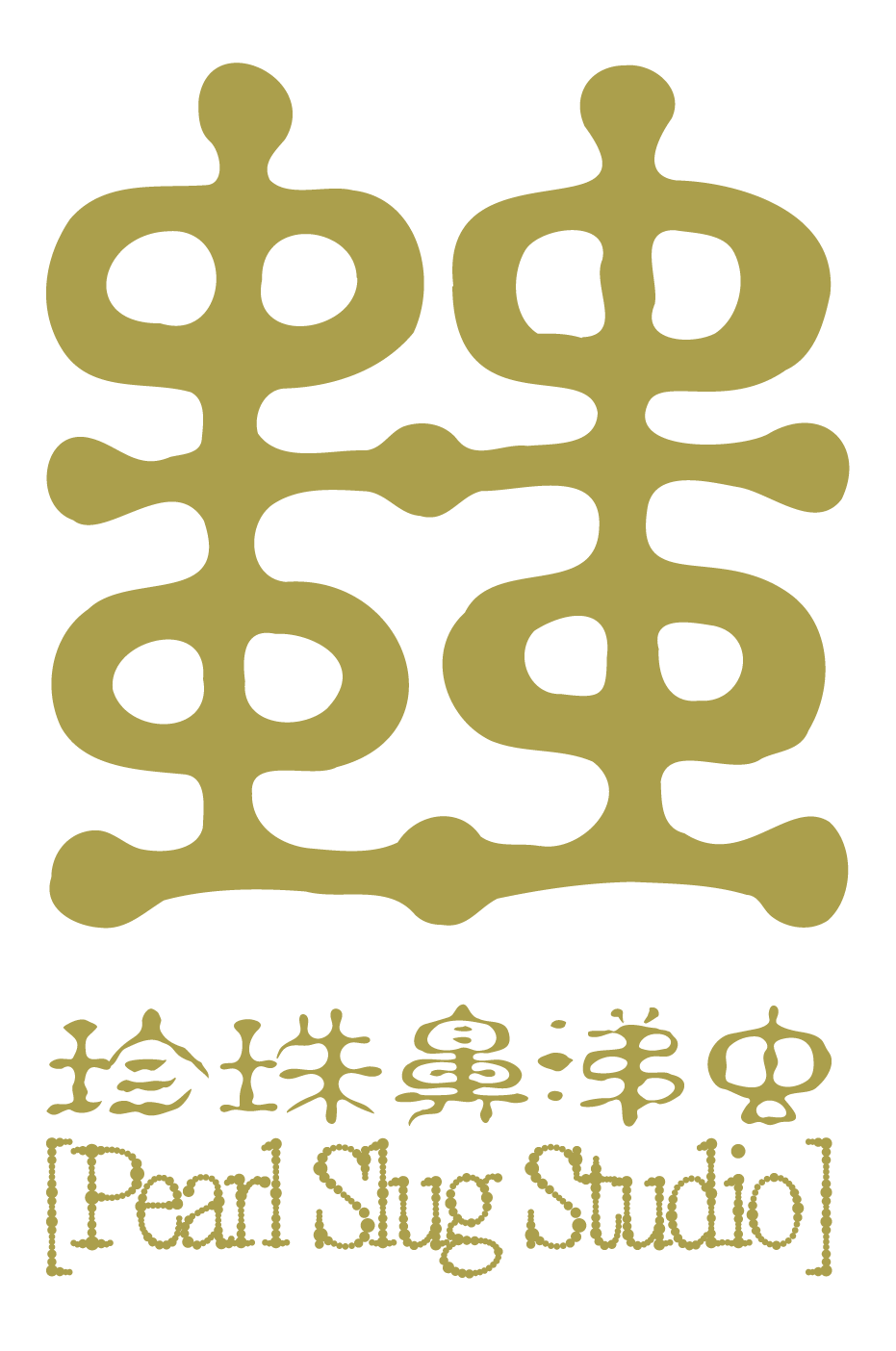在这一期的 Raging Vol. 001 坦塔罗斯之果里,我们刊登了一篇由毛麦郎带来的短篇小说《圆满》。针对如何解读《圆满》,主编酉良采访了作者本人,并将在本文中为大家呈现上一些答案,同时揭露一些相关的创作背景。
以下为采访内容正文:

酿:《圆满》的故事发生在海门,毛老师可以讲一讲海门这个地方吗?对于这个地方有怎样的感情与回忆呢?
毛:海门是一个毗邻上海的江北小城,夹在南通与上海之间,多年以来似乎都不能融入任何一方。当地的口号是“打造东上海”,但是去年我发现它又被归入南通行政区划了。我是在海门出生的,虽然一出生就随父母来了上海,但海门的农村算是我的老家。小时候逢年过节都会跟父母一起回老家,因此对海门的印象很大一部分都与「地方习俗」这些脱离我在上海的日常生活的事物有关。在《圆满》里你可以看到一些主人公「我」的视角里的海门的切片,海门既是我命定的故乡,也是一个怪诞的、陌生的地方。
我曾经不很喜欢海门,在我眼里它的城市干枯而静滞,它的乡村衰败而落后。我也一度相当厌恶我的出身,我想这也是我父母带我来到上海寻求向上的出路的必然结果。但事到如今我想我还是非常疏离地爱着这个不富裕的海边小城,我与它、与居住在这里的家人们有太多回忆了,很多和海门相关的记忆碎片经常无法控制地出现在我眼前。在我以前的一篇文章《海门回声》里提到过我和海门的一些关系,是我在看了另一位漫画家的同名作品后的即兴感想。我对海门的感情很复杂,因为它和我的根源有关。直到如今我都还在心中分析这些感情,随着我经历的增长我理清的头绪也越来越多。


酿:文中大篇幅的详细的描写了葬礼的过程,和我生长的地方相比,海门的葬礼习俗更复杂。作者对葬礼仪式的态度是批判又困惑的,我也同样困惑——在离开这个世界后或许获得自己的顿悟、明白了一切的奶奶为生者带来指示,遵循着这样的指示的生者们却仍然懦弱地用塑料、纸花和花色僵硬的布料装饰送别,生者遵循的到底是死者的指示还是习俗(就是几十代怯懦的生者堆积的逃避)的掩饰?
毛:“困惑”很明显,要说“批判”其实并不一定。我在写作时只是把我当时的感受忠实地记录下来,有一些自然是很情绪化的。至于“死者的指示”这一点,它则是一个心照不宣的谎言。中国的民俗里有“托梦”这一说,我认为只是生者相信或逼迫自己相信他们获得了死者的指示而已。我在结尾提到了「我」在经历了这一切以后的回答:我曾以为它是愚蠢,但它其实却是软弱,可我“不知怎么”并不反感这样的软弱。「我」把自己摆在了一个更剥离的位置,理解了一代又一代人为什么坚持这样做,它有时当然会是很笨拙的。
酿:在文章最后毛老师说自己理解并某种程度上接受了人类的软弱。尽管不知道毛老师为什么把文章命名为《圆满》,因为奶奶不甘的一生并不能算作圆满的一生,也不能断定因为人类自欺欺人地建立来生与转世的世界而真的相信奶奶在另一个世界获得了好的往生,但我仍在敲定英文标题的时候用了“A Full Circle”。因为我想无论往生与否,在一个人的生命如释重负地结束的时候,她与周围的人都想用自己的方式画下完满的一个句号。这是我的理解,我想问毛老师是为什么决定使用《圆满》作为标题的呢?
毛:我在写作时就认定《圆满》是一篇《局外人》式的故事,在默尔索身上我感受到了很多和我的相似性。「圆满」这个词来源于全书的结尾。如果方便的话我想摘录一下这一段:
「他走了以后,我也就静下来了。我筋疲力尽,扑倒在床上。我认为我是睡着了,因为醒来时我发现满天星光扫落在我脸上。田野上万籁作响,直传到我耳际。夜的气味,土地的气味,海水的气味,使我两鬓生凉。这夏夜奇妙的安静像潮水一样浸透了我的全身。这时,黑夜将尽,汽笛鸣叫起来了,它宣告着世人将开始新的行程,他们要去的天地从此与我永远无关痛痒。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起了妈妈。我似乎理解了她为什么要在晚年找一个“未婚夫”,为什么又玩起了“重新开始”的游戏。那边,那边也一样,在一个生命凄然而逝的养老院的周围,夜晚就像是一个令人伤感的间隙。如此接近死亡,妈妈一定感受到了解脱,因而准备再重新过一遍。任何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哭她。而我,我现在也感到自己准备好把一切再过一遍。好像刚才这场怒火清除了我心里的痛苦,掏空了我的七情六欲一样,现在我面对着这个充满了星光和默示的夜,第一次向这个冷漠的世界敞开了我的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融洽,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为了善始善终,功德圆满,为了不感到自己属于另类,我期望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前来看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
很残忍的一点是,奶奶死去的时候,无论如何愤懑或悲凉,她的一生都画上了句号。这是「圆满」讽刺的一层意味。另一层意义是,《圆满》归根结底不是关于奶奶的文章,是关于「我」的文章。「我」从与海门老家的互斥和割离中慢慢成长了,变得想要主动理解这一切、或是像默尔索一样被动接受这一切。通过一个仪式,我们看似给了奶奶一个答案、实则给了自己一个答案,葬礼送走了死者,但其本质是给了活着的人一个继续生活下去的理由——“你看,一切圆满解决了”这样的感觉。这篇文章也是我给奶奶和自己的一个完满的交代。我们的文化带给我的就是这样的体会,没有什么是真正圆满的,但人们总是愿意这么去相信。
酿:在《圆满》中有直接地描述奶奶面对自己死亡的心绪与她生前的不甘与愤懑,面对过很多次离别的人真的可以平静地面对与准备自己的离别吗?我想只有在每一个人自己的时刻到来时我们才能有所体会。毛老师的奶奶是一位非常坚强的女性,给毛老师带来了许多影响,这是因为我与毛老师有私交才了解到的,不知道毛老师愿不愿意讲一些奶奶的事情呢?
像奶奶这样不甘于自己的不幸、不屈于时代的不赏识的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却与荒唐的大笑和缭绕的烟雾共享最后的空气,我想这既是个人的不幸也是时代的不幸。我不知道奶奶是否在她人生的某个阶段也回头和这一切达成了共识,但或许就像毛老师的“接受”一样,“相信一种圆满”在我看来确实是一种和解。
梦里,奶奶的吊脚楼上因狂风暴雨而摧毁的笼子就像无征兆的离别,远去的亲人、朋友,无论因为什么而远去,都切实地从生活的漩涡里离开了。尽管这样奶奶却仍然安慰着自己它们会回来的,就像每一个人逃避失去的人一样,这像一个寓言故事。不知道毛老师能否为我们解读这个梦境?
毛:我不能说自己对奶奶很了解,但她仍是和我最亲的长辈。奶奶从小很宠爱我,但也偶尔责骂我,就像她责骂我的父亲和爷爷一样。奶奶不太懂得如何与家人相处,即便是与她最疼爱的我的妈妈也是这样。这样的家庭氛围也导致了我们家庭成员之间的隔阂和她自己的孤独,我有的时候觉得奶奶的遭遇似乎是注定的。
在她最后的几年里由于我在国外、父母离异和她的病情加重这样的客观因素,我与她实际上很少见面了,见了面也不再是小时候那个样子。这个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怀念记忆里的奶奶了,海门的一切从几年前开始变得很悲伤。
那个梦是真的,不属于这部小说里“小说”的部分。如果它像是某种寓言,它可能真的是,但我也不很明白其中的含义,只有梦里感受到的情绪使我印象深刻。反过来,可能正是情绪引导出了那个梦境也说不定,大脑和意识总是很奇妙。对于这样我也不太明白的事,我想读者也可以有自己的解读,就像那只夕阳下的山羊一样,它只是看着你。
酿:我非常喜欢这一段:“我站在一片黑暗的石子路上,看到远方的天空火光熊熊。夜幕不知道什么时候降临了。突然刮起了很大的风,带来了那里的锣鼓和唢呐声,十几里地以外,那里的人在歌舞和欢庆,他们围成一圈手拉着手,围绕着燃烧的纸屋跳着喜悦的舞蹈。有人癫狂地敲打器乐,有人大声喊叫和哭号,有人舞动起巨大的龙和狮子,有人在锅里熬煮血肉作成的汤。我伏在地上,以我的耳朵仔细去倾听,才突然明白他们在歌颂的是什么,才看清那堆火光里面被焚烧的东西。”
这一段描写应该是「我」出现的幻觉?文中描写的景象让我想起南方地区很多怪力乱神的祭奠仪式,「我」听到了什么?怎样的颂歌?火光里焚烧着什么东西?相应的,后面为什么会突然错觉地看见白鹤?不需要非常具体的解释,我只是非常好奇为什么会看见这样光怪又错乱的场景。
毛:这个和我的另一首诗有关,是对同一个幻觉的两种纪录。前半段是真实的经历,也是在一个傍晚在奶奶家的附近遭遇的;后半段是一些模糊不清的联想,为奶奶守灵的几个晚上都是听着这样的声音度过的,画面也基本是那几个白天里看到的。至于这个场景指向什么,我不太想在这里揭示什么具体的答案,读者会有自己的理解。
白鹤的场景也是在守灵的夜晚里梦到的、白天所看见的场面,垃圾袋套在竹竿上变成了白鹤这样有中国古典意境的动物。你说它是讽刺也好,是意识对现实的美化也好,同样地,没有明确的指向。有一种说法说,生活、神明、或是上天总是会在某些你注意不到的地方给你提示,你只是需要发现和理解它们的眼睛。很多人因此走向了神秘学、符号学、神学之类的道路,我也很难保持纯粹而盲目的唯物主义。
附上那首诗吧:
《行街》
夜幕降下的时候
风把锣鼓的声音传来了。
离这里十几里地的地方
人们在歌舞、焚烧纸屋,
火光冲天而起
光照亮整个南方的天空
有人死了,
或者有人在那里出生
他们舞起了巨大的狮子
他们枪杀了所有描绘风光的诗人,
他们喊叫、他们哭号
他们挥舞着长矛驱赶燃烧的巨象
他们以神的名义
焚掉经文、推倒古老的石雕。
一切都记录在风里
风把一切都传到了我的眼
和我的耳里。
酿:《圆满》如果有味觉的话,应该像在吃鞭炮纸屑,客观来讲没有任何味道,可能隐约有些泛苦,吃下去后老觉得半夜会在胃里像鞭炮一样噼里啪啦地炸起来。但苦涩之间,在文章的最后一段提到了产自常乐的、非常甜的草莓,草莓有着怎样的寓意呢?
毛:感谢你有趣的联觉!关于文章里用到的意象的寓意,说得太多太具体的话就变得有点像中学时候的阅读理解般造作了。但是在一个苦涩的、可怖的故事的末尾回归到甜美的平静是我非常钟意的结尾方式,在很多电影和小说甚至音乐里都有这种手法的运用。
在我小时候读过一篇短篇小说,讲述了一个荒诞的噩梦:主人公从睡梦中醒来发现院子里站满了人,每一个人都试图闯进来,并试图用交媾和繁衍来强化群体的数量,婴儿一落地就成长为人,最后院子里的人越来越多、场景越来越血腥,不断有人在尖叫中被挤成肉酱。在窗户快要被压碎的时候她终于从噩梦里醒来,发现只是门铃在响,原来是外婆为她送来了美味的晚饭。这种把美味的食物当作物质世界里的慰藉、宣告某种黑暗的终结的手法也是非常能体现某些象征意义的。
「常乐镇」这个地名我非常喜欢,从小就一直听长辈提到,实际上是个没有什么特点的小镇。在这个漫长噩梦的最后,爷爷告诉了我关于海门的、我所不知道的新的事情,也算是海门给我的慰藉了。

↑
Instagram
@PearlSlugStudio
Wechat/微信公众号
@珍珠鼻涕虫PearlSlug
@PearlSlugStudio
Wechat/微信公众号
@珍珠鼻涕虫PearlSlug
*♪¸¸.•*¨・:*ೄ·⋆*❁*⋆ฺ。*.·˖*✩⡱ Contact Us *♪¸¸.•*¨・:*ೄ·⋆*❁*⋆ฺ。*.·˖*✩⡱ Contact Us *♪¸¸.•*¨・:*ೄ·⋆*❁*⋆ฺ。*.·˖*✩⡱ Contact Us *♪¸¸.•*¨・:*ೄ·⋆*❁*⋆ฺ。*.·˖*✩⡱Contact Us *♪¸¸.•*¨・:*ೄ ·⋆*❁*⋆ฺ。 ·⋆*❁*⋆ฺ。 ↑↑